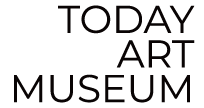我在、他在
——于轶文绘画艺术
对于轶文绘画艺术的见解,单从画面进行视觉察阅是不够的,只有整体考量他创作这批作品的心路历程及其行为方式,才能较为全面而贴合地作解读。在他个展之际,对他作品常态的外象与内质析评,定然有不少同仁发声。本着“见仁见智”的学理逻辑,或从个人向度谈点感受与见解,应该说对了解于轶文其人其艺是有所补益的。
在绘画创作中,农村题材一直长盛不衰,但多是抱着猎奇的心理,浮光掠影式地攫取乡土、民间的风情与民俗;抑或以一种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话语方式来言说边地农村的僻荒、没落和原始。如何深刻地揭示农村、农民在今日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矛盾的冲突、命运的困顿、生存的异化,尤其是将艺术家的人格立场融入其中,则为许多艺术家所忽略。于轶文从不以这种“他者”的立场和目光游离于所要表现的物象之外,而是以“我在”的介入方式去认识和体悟农村、农人的“他在”。十余年来,他以一种背弃潮流和世俗生活的艺术方式进行着他的绘画创作实践,几乎把所有创作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湖南湘西一个叫凉灯村的偏远山乡,投入到村中一位孤独、苦涩老人龙升平的生活中。他与老人朝夕相处,把盏促膝。十年间,执拗地面对同一形象,同一环境,作持续而深入的人文思考和视像表达。于轶文这种不合时宜的艺术创造方式,虽然几近偏执,却的确令人感动。
在经历了纷杂多变的现代艺术洗礼后,作为青年艺术家的于轶文,或许是有感于当代艺术在现实功利、个人欲望和资本操作挤压下,越来越失去了它原有的纯粹性和尊严;抑或乡村、乡民本来就是他难以排遣的一个文化情结。总之,他一直就不屑于那种对新艺术体验的热切追求,那种历险似的大胆尝试,那种创造新潮的挑战姿态,而悄然回归的是一种朴素的、有教养的,对法则和伦理的肯定和尊重。他以近乎圣徒般的行为方式,一头扎进滋养他成长的凉灯村。在那里,他意图建构一个本体自由、本体真实、无功利的、非异化的、超验的艺术世界,以此来抵御和消解虚伪、颓靡的社会现实。
因了文章言说的题目,在这里有必要对“我在”与“他在”作一些理论上的注解,以便下文的表述。
所谓“我在”与“他在”,颇有点存在主义哲学意味,其实质则是中国古典美学关于“主体”与“客体”,即“我”与“物”关系的至高命题。明代心学哲人王阳明对这一命题归结出“心外无物”之说。一次,王阳明和友人出游,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答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之外。”花与我的关系,亦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自开自落的花,不是人的对象物,无价值;而当你看此花时,花作为人们的欣赏对象,是人感情的寄托物,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花因“我在”的启动,才有“他在”的可能。倘若“我在”不针对花启动,这花存不存在?存在的价值度怎样?于我而言,不仅不重要,连它是否真实存在也受到质疑。
王国维先生所撰《人间词话》中,对“我在”与“他在”这一关系具体运用到艺术创作里,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补充:“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文中强调的“有我之境”、“物著我色”不仅与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近义,还进一步阐明了“我在”是能动的,“他在”是被动的,“他在”的意义因“我在”而获得。景物因人的注视才有了意义,这意义也定会映上人的思想和情感色彩。
二王从中国历代美学思想中提炼出的审美哲思观和艺术创造观,很显然都立足于“我在”,即重主体,重人本精神观照。换言之,也就是注重主体自觉。在艺术创造中,作为主体的人,应自发地以己度物,用个体的生命去感受他者的生命,去感受自然的生命。
很显然,于轶文凉灯村十余年的坚守,可以说是遵循这一艺术创造观的典型范例。他以贴近的、深度的“我在”方式,介入龙升平老人的世界,没有居高临下的悲悯,也没有隔岸度物的冷漠,而取真诚、亲和、交融的态度,在持之以恒的日常体察中去感知老人的精神世界、生命世界,进而作生存意义、生命意义的思考、叩问和揭示。
广览于轶文十年间在凉灯村所创作的油画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作品中,他以老人为主体创造的图像景观,不管是各式形态组合而成的老人形象,还是对老人宅屋生活场景与家什的单独描绘,无不深深烙上了于轶文人本精神观照下的文化印记和道德印记,充盈着浓烈的人性关怀和文化情思。我在阅读于轶文作品时,不仅感叹作品中老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更是感叹于轶文这种深度投入的行为方式。我认为,这种深沉的人本观照精神,这种极端的“我在”自觉态度,无疑给于轶文绘画艺术的感染力增添了不少筹码。
另外,于轶文的绘画艺术还具有较强的“比德”美学特点。“比德”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概念,是指在艺术创造中,借“他在”来寄寓“我在”的思想、情感;或借所描述的客体来隐喻创作主体的文化追求与人格操守。在艺术创造中,创造者在选取创作题材或描绘客观物象时,常有审美情感和文化立场上的占位。客体对象能否成为创作主体的审美对象,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创作主体的道德观念与文化观念。也就是说,客体对象的某些特点和创作者的道德属性、文化属性是否有着某种一致性。因此,创作者在创造中有倾向性地去选择表现对象,并把对象与自己联系起来,作为一种道德观和文化观的象征。这种象征和隐喻关系,就是所谓的“比德”式艺术创造。
在于轶文的作品中,龙升平的形象是贯穿他绘画创作的主体图形,这一主体图形与景物的转换与配置,经他精心营构所达成的视觉认知和文化向度清晰而明确,既真实记录和反映了龙升平老人的生存常态,更是他人文情怀投射下的借物言志。他笔下的老人形象决非一般意义上个性化的人物,尽管他作品所有的表述都是围绕单一的个体——龙升平老人在进行,也力图通过老人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用品细节去展示老人独特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但我仍然认为,他对龙升平老人这一单体形象全方位的描绘,带有强烈的类型化(抽象化)倾向。尽管他采用的是写实性语言,但已然超越了对客体物象“再现”式的被动描摹,所要向观者呈示的不再是状物察形等写实绘画的基本功能,也不完全是言情体性等通俗欣赏层面的一般审美表达。他完全把老人及其生活景物的具象形态符号化、观念化了,并以一种心象交融、心象合一的手法创造出独特的视图样式。在我看来,于轶文这种看似写实化、个性化的形象创造和景物描写,已明显注入类型化和隐喻性的成份,这就好比中国水墨画中对梅、兰、竹、菊一类题材的描绘一样,看似具象写实,实则符号化、隐喻象征化了。
挪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来讨论于轶文的油画艺术创作,不无牵强之嫌,但这仅为个人的注视视角和见解。于轶文在自己的油画艺术中所秉持的文化观、艺术创造观,以及他特立独行的艺术实践,无不透显着“比徳”美学的精神气质,同时也是人本精神观照的最好注脚。于轶文对自己艺术道途的坚守,有如一个文化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其姿态固然孤独,但较之当下过多的文化“热点”和世俗文化洪流,而显出一种罕见的高贵。